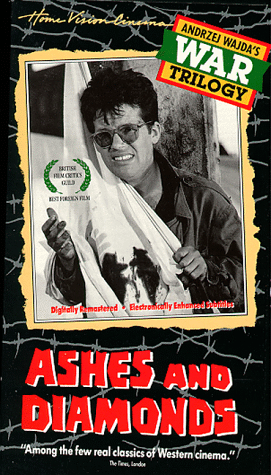WAJDA ANDRZEJ 《灰烬与钻石》
波兰导演华依达(1927--- ),生于波兰的国际大导演,从影50年,其一生经历了波兰近50年来的重大变革,见证从二战残灰中重生的波兰,动乱中的70,80年代以及混乱的团结工会时代。其作品一再体现时代嬗变的多样面貌,并赋予历史新的意义。
代表作:58年《灰烬与钻石》、57年《下水道》、77年《大理石人》、81年《波兰铁人》、82年《丹顿事件》、83年《柏林之恋》、及87年《附魔者》等等
《灰烬与钻石》是其战争三部曲的首部,获得当年“英国电影学院评论大奖”,也被列入世界世纪最佳百部电影之列。
导演在《魔法师的宝典——导演理念的构思与透视》一书中谈到:
在过往30年间,世界已经完全改变,对冷战的持续恐慌使我们对其它民族的情况更为关注,因为在随时随地可能爆发局部战争的威胁下,我们的生活与别人的所为所不为密切相关….如果你想了解别的国家,还有比亲眼所见来得更深切吗?我们电影工作者,正可经由我们的取材及影象将不为大多数人了解的遥远国度呈现眼前。二战后,我们对外界的视野主要来自美国片。经过《忠勇之家》我们体会到英国对法西斯的抵抗;经过《桂河大桥》我们见识了日本法西斯的残忍;经过《纽伦堡审判》我们看见德国战后的景象,水而罗塞里尼的《不设防的城市》雷尼.克来曼的《铁路英列传》则开启了对战争的另一种视窗,使我们得以从全新的角度看待战争。在此,战争不是好莱坞式的复制现实。而是在罪行现场的逼真面貌。
《下水道》和《灰烬与钻石》正是以世界电影新生国家之发言者状态而面世,和罗塞里尼一样为时代留下记录。当时,我们无法和法国与意大利电影业相比,他们享有充足的经验,我们的演员则不为人知。虽然有种种缺失,他们作为目击证人的地位,是货真价实的。
许多国家都在期待“本土电影的出现”,以呈现本国特有的生活情绪:快乐,冲突及关注。
许多掌故、桌边随心之语、报纸上的琐事,甚至尼在街上听到的只言片语都可能具有悲剧性,但前提是你必须从这些片段中萃取出其深意,找出真正的英雄,同时决定叙事者将持的观点。《灰烬与钻石》影片中的主角不是原著中的主角党书记 茨祖卡,而是破坏分子马齐克,为何如此?因为茨祖卡的理念只有通过马齐克体现。
在原著中,故事进行的时间是1945年5月的某两个星期,但电影中被压缩成24小时多一点:一天、一夜及第二天的清晨。当时的想法是将现场放在大战的\最后一夜及和平来临的第一个清晨,充满了无限希望的情景,随后发生的事情却使个人的希望崩溃,这整个安排会使观众受到意外地震慑。
对话的艺术
年轻时,电影中的对话被认为是必要之恶,只要你觉得无法用影象表达时,就插入一段对话。这许多年来,人们总是一再地向我们抱怨波兰电影中的对话有多糟——不幸的是,他们说对了。或者应该说,波兰演员在银幕上说话时多么拙劣—— 他们又说对了。今天,情况全变了,波兰电影已和其他国家电影一般滔滔雄辩。巴扬(FILIP BAJON)、贺兰(AGNIESZKA HOLLAND)、奇斯劳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赞努西(KRZYSTOF ZANUSSI)、马杰斯基(WOJCIECH MARCZEWSKI)等导演在处理\自己的片子中的对话时,心中总是随时考虑着影片的情节、角色特质及将在电影中说这些话的演员。正是经由这些波兰电影工作者的努力,现在大家对波兰语的对话已不再感到刺耳了。先前的排斥心理源自传统上电影几乎不用波兰语发音。我年轻的时候,我们的电影说的是英语、法语或意大利语。你可以想象,当柏格曼在荧幕上用一种没人听得的语言说话时,我们有多么惊讶!当时,每年寥寥几部电影并不足以说服波兰人民,波兰语适合在银幕上出现,从我们的观点而言,战后世界的重要文化现象之一,便是波兰语电影在世界广为流传。
每部电影总需要有人来写对话。但一个专写对白或琢磨别人对白的人,并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称职的对白写作者是稀有动物。因为导演们总是想尽各种偏方来解决这个问题。假使剧本改编自文学作品。则对白通常是简单地将原著移植过来。问题出在,这样的对白适合阅读,但从银幕上听起来就显得不真实。有的导演将原著视若粪土,和演员们分赃般若粪土,和演员们分赃般地按照各自的才华及戏份将它重新写过。有的则仅提供演员们一些概括性的概念,要他们即席发挥。即兴演出的问题出在:对白往往沦为无意义、机械式的喃喃自语,像一群醉酒失去理智的人,无法推动情节进行,与影片的韵律节奏格格不入。
介于两者之间的极少数演员可以体认导演的意向,了解自己的人格特质、与即将扮演的角色个性,将之有机融合于其临场蹦现的独立与对白中。一个成功的例证是丹尼尔.欧布利希斯基(DANIEL OLBRYCHSKI)在我的片子《桦木林》(BIRCHWOOD)中与女儿的对话。片子拍到一半时,丹尼尔已深深体会了自己的情况及角色的需要。加上他女儿根本不了解他在说什么而无法回答。他作了一篇光彩耀人的即兴式演说。
纵然如此,还是有一些对话无法用以上的方法演出。我想到以下这个例证:
警察:你今年几岁?
男孩:一百岁。
警察(抓着男孩):你今年几岁?
男孩:一百零一岁。
没有演员可以临场想到这么灵光一现的一幕。这需要\真正的作家——以上的例证正是出自《灰烬与钻石》编剧杰西.安德瑞斯基的手笔。
对白写作者往往为了追求对白的“自然”,而使它沦为无意义的杂音,成为影片之诸多声轨之一。他们总是尽力说服我们这些导演,那才是最复合乎潮流的写法,其他方式不值一顾。问题出在,大多数影片对白之所以似曾相似,是因为“质”的关系。导演在对白无法担负起推动整部影片前进的责任后,便只好推而求其次的和一大堆对话缠斗。顶多只能营造某些气氛罢了。如果是个成功的剧本,你可以把所有的叙述省略不读,只读对白本身就可以了(我建议任何打算走这条路的人在真正去做之前,可以先试试看)。